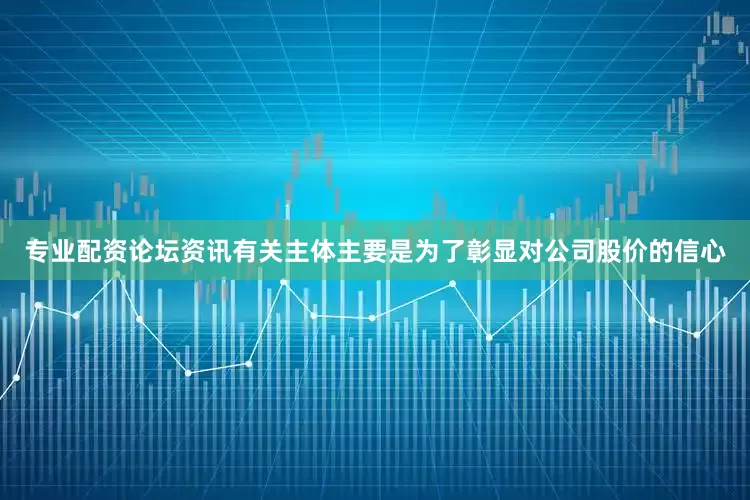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刘宗智
文学是长在故乡的树。纪录片《文学的故乡》第二季近日开播,纪录片延续“文学回乡”的核心母题,聚焦作家韩少功、张炜、翟永明、叶兆言、刘亮程、莫言,在文学现场探寻文学生长的源头,从首季的小说扩展至戏剧、诗歌、散文等文学体裁,力求拓展文学影像表达的新维度,同时也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高度和广度。
归乡觅源
故乡,是文学永恒的话题。故乡,不仅代表着地域的归属感,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情感寄托。导演张同道说:“《文学的故乡》并非作家传记,也不是作品的读解,而是讲述作家如何把生活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。”作家创作缘起何处?如何调动故乡和童年记忆创作出艺术作品?这是本片的拍摄重点,也是难点所在。
“返乡”,成为贯穿影片的情感主线与结构线索。摄制组跟随作家的脚步,行走于山野田畴与街巷阡陌之间,在真实的还乡场景中,编织起层次丰富的叙事网络。每集伊始,创作团队都向作家提出返乡的请求,即便像毕飞宇这样对故乡的记忆已然模糊的对象,返乡也同样是不可回避的流程之一。
接下来的叙述都是围绕跟拍返乡过程而自然展开,逐步再现作家的孕育、成长和创作过程。以《毕飞宇》一集为例,从他在扬州大学求学时对文学的痴迷喜爱,到毕业后就近《南京日报》租房蛰伏,进行创作风格从先锋小说向写实小说、从语言实验向小说人物的转变,在《花城》发表处女作《孤岛》,到创作《青衣》后实现对小说结构和人物塑造方法的突破,再到王家村、陆王小学、杨家庄、杨家小学等地探访,逐一展现作家的生活经历及创作缘起、经过。

从人物原型到地方风物,故乡为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,这也成为影片着力表现的内容之一。莫言的高密东北乡,胶河、高粱等自然地理元素,茂腔、年画等民间文艺,成为作家驰骋想象的宝贵资源,使其构想了浓郁、奔放的文学王国;阿来的故乡雪山高耸,建筑充满民族风情;迟子建故乡大兴安岭下的北极村冰封雪飘,北国风光浓郁;毕飞宇故乡位于秀丽的江南水乡,四周水泊纵横;贾平凹的商洛文化中,秦腔、社火、民歌及西北地区的乡土民风,使作家在头脑中孕育出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。
根脉所系
故乡,是作家创作的源泉,也是他们心灵的归宿。莫言第一次回到旧居时说:“所有的小说的原点就在这里。”这样的认知,在他千方百计想要离开家乡的青年时代尚未形成。但是,莫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《春夜雨霏霏》,使莫言登上中国文坛的《透明的红萝卜》,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和思想情感都深深植根于他那个原点而成,只是当时还没有很自觉地认识到而已。按照莫言自己的说法,“高密东北乡”等字样最早出现在其小说《秋水》中,从此它“就慢慢变成一种我的文学地标了\",甚至可以“一辈子就写这块小地方”。

童年时饱受饥饿之苦的莫言回忆起那段岁月,坦言“(人在饥饿面前)什么面子啊、尊严啊,实际上都是轻如鸿毛。这也让我从小就看到了人的底线,了解到人在生存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,很多人性都会发生严重的扭曲。”源于这样的生命体验,莫言在小说中对饥饿的呈现是多样的。比如《生死疲劳》中,莫言特意塑造了一个西门屯建屯一百五十年历史上“最馋”的小孩形象。小说中描写这个小孩“莫言”在养猪大会的现场,为了喝到大缸里残留的糖水,将整个上半身都钻到了缸里,拿铁勺将缸里仅剩的一层糖水刮干净,最后又将整个水缸掀翻,钻到缸里用舌头舔食。乍一看,这个名叫“莫言”的孩子吃相如此夸张,但其实这是作家莫言对自己的一种调侃和回忆。
当被人问及,“你短篇小说集里边有很多孩子都是出了门,沿着胡同往北跑,然后到了河堤又往西跑,过了桥又往西跑,为什么都是这个方向?”莫言回答:“这就是我的村庄的方向,我家的方向。”在莫言内心深处,“作家的故乡,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,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。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,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,这地方是你的血地。”
影像求索
如何将抽象的心理戏剧与不可见的“文学性”转化为具象的影像?《文学的故乡》做出了富有创造力的尝试。
故乡隐藏着作家的童年、成长与最初的感知,一旦回到故乡,所有记忆都将被激活,可能随机进发出精彩的纪实场景,作品里写过的地方、写作的地方、留下童年记忆的地方,都成为了纪录片里鲜活的文学现场。

莫言回到家里,用高密话请95岁的父亲去县城过生日,父亲坚决拒绝。莫言又说又写,反复劝解,父亲才勉强同意,却突然问道:“家里还有馍,还有烟,要不要带上?”贾平凹走进秦岭深处的村庄,看见炊烟升起的房子,三句两句便与一位农妇拉上家常,走过去帮着炒菜,仿佛多年邻居;刘震云回到老庄,碰见一位养鸡的老乡,老乡当即表扬刘震云在北大的演讲好,关键是收尾收得好;迟子建回北极村,一见白桦林便情不自禁地躺在雪地上,全然忘了零下40度的现实情况;韩少功及夫人驱车行进途中,看到熟悉中略带陌生的山道,两人回忆起当年开垦茶场的场景;张炜在芦青河河畔徘徊,偶遇撒网渔民,攀登莱山时,与在此居住多年的修行人士感慨一潭好水。这些镜头无法还原,无法调度,也不可预测,但最富于情感张力与戏剧效果。

《文学的故乡》放弃宏大叙事,回归质朴独白,作家们的乡音为影片增添了粗粝而真挚的情感色彩。韩少功娓娓道来:“马桥的中心,就是两棵枫树。没有哪个娃仔,不曾呼吸过它的树阴,吸吮过它的蝉鸣……”画面配合以俯拍的青色密林,树叶交叠摇曳,日光渗漏,营造出亦真亦假、如梦似幻的氛围。
在作家自述之外,影片还拓展了评论视角。摄制组远赴多国,采访30多位汉学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与诺贝尔文学奖评委,记录下中国文学走向世界、莫言荣获诺奖的历程。
意蕴相生
为保留真实的质感,《文学的故乡》多采用长镜头跟踪拍摄,捕捉作家还乡过程中的情感悸动、眼神闪烁,以及与亲友乡邻的真诚交流。迟子建回北极村旧居与新住户交流,毕飞宇回中堡镇老街偶遇许木匠,木匠认出之后伸出热情的双手大喊“毕飞宇”,导演张同道直言,“如果没有抓拍到就会永远错过这些场景,即便排练都无法重现。巴郎山,爬上海拔4400米高峰,还要抢拍阿来寻找植物的场景。这些情景来不及构思,只能凭本能的直觉和丰厚的经验准确、细腻、美学地捕捉下来。”从空中航拍观看作家在大地山川上的活动,作家仿佛故乡土地上一棵行走的树,一株活动的庄稼。

对于部分难以实景呈现的内容,创作组以搬演方式进行意象化还原。如莫言《透明的红萝卜》中瘦弱的黑孩,由村庄中的少年扮演,在草丛中放羊,谷地里抓蚂蚱,独自游荡于田野,背景刻意规避现代元素。这种再现力求节制、素朴,旨在为观众开辟一条进入文学与历史的影像通道。

《文学的故乡》更致力于为每位作家寻找一个核心意象,既有现实依据,又具象征意蕴。《莫言》一集里反复出现的是一位民间说书艺人,他在田间地头、桥上树下摆出小鼓,用高密茂腔、山东快书、西河大鼓演唱莫言的打油诗;《贾平凹》篇里,一位农民在油画般层层叠叠的远山前锄地,迎着日头,步步向前;刘震云则是两种意象的交叉:人群里的刘震云侃侃而谈,发表演讲、接受采访,独处的刘震云静默、读书、写作、思考,媒介里的名人与生活中的作家两幅侧影相得益彰。最新一季中,影片还采用了动画与实景结合,用不同的动物象征作家,比如韩少功对应凤凰,张炜对应大象,构建出“超以象外,得其环中”的艺术境界。

《文学的故乡》以平等的对话,使作家笔下的故乡不再仅仅属于个人,也成为可供所有人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。故乡与文学,就在这样的交替中,彼此相融,生生不息。
新闻线索报料通道:应用市场下载“齐鲁壹点”APP,或搜索微信小程序“齐鲁壹点”,全省800位记者在线等你来报料!
股票10倍杠杆怎么操作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